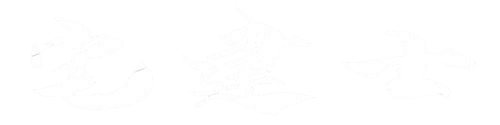共计 1936 个字符,预计需要花费 5 分钟才能阅读完成。

四月下旬,当第 217 届通常国会来到预算审议的尾声,众院内阁委员会里弥漫的气氛却丝毫没有“例行公事”的松弛。国民民主党议员菊池大二郎挥舞着一沓厚厚的调查报告,直指防卫省市谷本部投影在会议室大屏的卫星图:“如果连这里一公里范围都挡不住外国资金流入,我们还谈什么经济安全?”他所说的“这里”,正是去年底政府依《重要土地利用规制法》发布的首份年报中,列出的三百七十一宗外资交易的重灾区——东京都市谷一带,仅在防卫省周边就记录了一百零四宗土地或建筑过户。这份数据虽然只占全国 399 处“监视/特别监视区域”内所有流转的不动产 2% 出头,却因为触及基地、港口、通信枢纽与国境离岛等关键设施,一夜之间点燃了国会与舆论对“外国人购地”的警觉与焦虑。
如果把视线拉远一点,日本对外资购地的立法轨迹其实并不漫长。2022 年 9 月甫一施行的《重要土地利用规制法》,在当时被誉为经济安全保障“三支柱”之一:政府得以围绕自卫队设施、原子能装置以及人口稀少离岛划出约一公里半径的“监视区域”,其中敏感度更高者提升为“特别监视区域”,大额交易须事前申报,违法者理论上可面临用途限制乃至强制收回。两年过去,数字化地籍尚不到六成覆盖、部门间信息孤岛依旧林立,最醒目的结果却是:面对三百多笔疑点清晰的外资买卖,政府没有对任何一件发出警告或使用中止命令。法律的“牙齿”或许已经长出,却似乎还未真正咬合。
这一漏洞首先暴露在“国籍信息”的盲区上。日本的不动产登记并不记载所有者国籍,基层行政机关往往要等交易完成、文件递送法务局之后,才辗转得知买家身份;而当买家背后还有跨境信托、特殊目的公司或多层股权架构时,“真正受益者”究竟是谁,常常淹没在纸面迷雾之中。其次,“一公里”这一看似科学的警戒圈,也正被新兴技术的突进迅速稀释:高功率定向天线、光纤监听与军民两用无人机,使得千米之外一样可以对卫星通信或电磁频谱构成威胁。于是越来越多的议员在委员会上质疑:既然雷达站、陆上自卫队地下通信电缆登陆点、水源涵养林同样至关重要,为什么它们往往处在监视区的“边线之外”?
然而在“收紧”的呼声背后,日本又不能忽视自己的另一重身份——全球资本最看好的成熟市场之一。弱日元与零利率正在把美欧机构的目光吸引到东京、大阪与福冈的写字楼、物流仓库、数据中心,甚至人口急剧外流的地方小镇。根据年报统计,中国内地买家在三百七十一宗交易里以两百零三宗居首,韩国、台湾随后;但如果放大至金额或者建筑类型,又能发现大额且与国土安全最相关的地区,往往并非单一国籍主导,而是混杂着美国与英联邦的养老基金、私募 REITs 与家族办公室。在北海道二世谷,外资创造的高档度假村与滑雪公寓既抬高了地价,也撑起了地方财政;而在对马岛或石垣岛,类似的买卖则被当地议会视为“蚕食领土”的潜在隐患——一体两面,都是现实。
正因如此,政府对“升级版立法”始终态度谨慎。木内实经济安保担当相在四月质询的最后十分钟里,反复提到“兼顾国际义务”与“对内外一视同仁的用途管制”。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,日本对服务贸易列有“国民待遇保留”的项目极少;若突然对特定国籍或外资整体实施准入前禁令,不光可能引来对等报复,还会冲击日本仍赖以摆脱通缩阴影的不动产市场。跨党派的“外国人土地取得规制法案”因此提出折衷路径:维持所有权开放,但把长期租赁、信托受益权、甚至超过十年包租的运营合同都纳入申报;同时设立直属首相官邸的“土地取得对策推进本部”,用统一的 KYC 框架将土地登记、金融账户、公司受益者信息打通。不少执政党议员私下承认,这或许才是日本能在“吸引资本”与“保障安全”之间勉强找到的平衡点。
真正棘手的问题在地方层面发酵。人口老化率超过六成的北海道深山村落,几乎把林业用地当成廉价的“债务减免器”向外资抛售,盼望下一轮度假市场能带来新的就业;而受疫情与原材料涨价拖累的长野、妙高等滑雪胜地,则担心中央“一禁了之”会让外资止步,导致停工烂尾。国会山里一纸法案的每一次修辞变化,都可能在千里之外的雪道、渔港或温泉老街激起截然不同的涟漪。
从三百七十一宗到下一年的数字,究竟会是三百七十二、五百,还是在强监管之下突然急剧下滑?答案不会只写在内阁会议纪录里。它将取决于地籍数字化能否提速覆盖,取决于国会能否在党派纷争中提出可操作的跨部门平台,取决于日本在多边谈判桌上如何解释“国家安全例外”,也取决于弱日元周期里海外资本对“风险—收益”这座天平的新判断。土地买卖的账簿背后,是一个老龄化国家在主权、安全、开放和复兴之间摇摆寻找的分寸——那条界线若隐若现,却又关乎日本自我定位的核心命题:在世界舞台上,是要重筑高墙,还是继续向外界敞开大门,抑或两者之间,划出一条精细而漫长的安全走廊。